北宋官员高薪历代罕有为何仍未能养廉探究1840至1949年思维导图中的权威视角
北宋官员高俸历代罕见,为何仍未能“养廉”?探究1840至1949年思维导图中的权威视角

北宋官员的俸禄之优厚,在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中是数一数二的。据《宋史·职官志》的记载,宰相、枢密使一级的,每月俸钱三百千(即三百贯),春、冬服各绫二十匹、绢三十匹、绵百两,禄粟月一百石;地方州县官员,大县(万户以上)县令每月二十千,小县县令每月十二千,禄粟月五至三石。正俸之外,还有各种补贴,如茶、酒、厨料、薪、蒿、炭、盐诸物以至喂马的草料及随身差役的衣粮、伙食费等,数量皆相当可观。
宋真宗时外任官员不得携带家属,而家属的赡养费则由官府财政供应,月供米面羊等生活用品。此外,还有“公用钱”。如节度使兼使相公用钱可高达二万贯,而且上不封顶,“用尽续给,不限年月”。公用钱之外,又有“职田”。诸路职官,一律有职田,其中两京、大藩府四十顷,次藩镇三十五顷,而直至边远的小县尚有七顷。且“外官占田,大逾往制”,由佃户租种,官员坐享其成。

北宋实行高俸制,其目的在于养廉。这在北宋皇帝及其大臣们的心目中是十分明确的。正如宋太宗所说:“廪禄之制宜从优异庶几丰泰责之廉隅。”因此,从太祖至徽宗,都曾为百 官养廉而不断增俸。
少数官员也曾提出高俸养廉问题,如范仲淹在《庆历新政》施政纲领中就提出:“养贤之方必先厚禄禄厚然后可以责廉隅。”王安石在熙宁变法期间,不仅增了官俸,而且发出了吏禄。此前官方与吏习惯上通称为官方,但在宋代,有严格区别。在朝廷除授,并按规定领取资偿。而吏则或出自召募,或应差役,是各级官方及其下属部门办事人员,无资偿靠克扣受贿和侵渔百姓为生。

《续资治通鉴长编》对恶吏赃吏多有揭露,如熙宁三年八月神宗发现仓吏侵克欺盗军粮严重,因而下令创立“仓法”,本着增禄不厚不可以责其廉谨指导思想首先给仓吏以厚禄岁额一万八千九百贯。但同时又立法对赃贿者施以重罚:若再侵克受贿计赃钱不满一 百徒一年,每一百加一等;一千流二千里,每 一千加一等罪止流三 千里配五 百里外牢城流罪配千 里内品满十 千即受赃为首者配沙门岛。(详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14)
此后,“仓法”逐步推及内外吏,以至熙宁六年正 月已达十七万 一 千五 百余 贯。王安石曾向神宗表白:“今取于民鲜,而 君子知自重,此臣等推行 之 本意也。”

但实施效果并非决策者主观想象中的那么乐观。“本意”如此善良,却让实现不了预期结果。一方面,由于赏金激励,使得原本应该被打击的一些人因为恐惧而暂时改邪归正,这样做虽然减少了一些问题,但并没有根本解决问题。一方面,即便如此,这样的措施也不可能完全阻止所有的人都不会犯错,因为人性的复杂性和欲望难以彻底根除。
另外,由于增加了大量新的岗位和津贴,加上因经济状况变化导致国家财政负担日益增长,这种制度最终只能导致更多的问题,比如过度膨胀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以及国家财政上的压力越来越大,最终导致了经济形势更加严峻的情况出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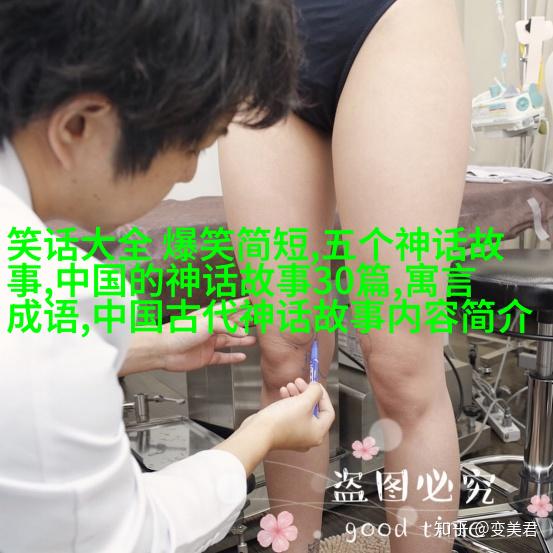
总结来说,如果把现实中人性的复杂性看得太简单地认为,只要提高他们的物质利益,就能够改变他们行为,那么这样的认识误区就会让我们无法真正理解和解决问题。其实,对于那些想要通过提高收入来防止腐败的手段来说,更重要的是建立一个透明、高效且能够有效监控系统,以及培育一种普遍存在道德规范,同时还需要确保这些规章制度得到执行。这才是更实际有效的手段去避免腐败现象发生。而单纯依赖金钱手段来控制人的行为,则显然是不够用的,也许会产生一些短期效果,但长远来看并不具有持久性。



